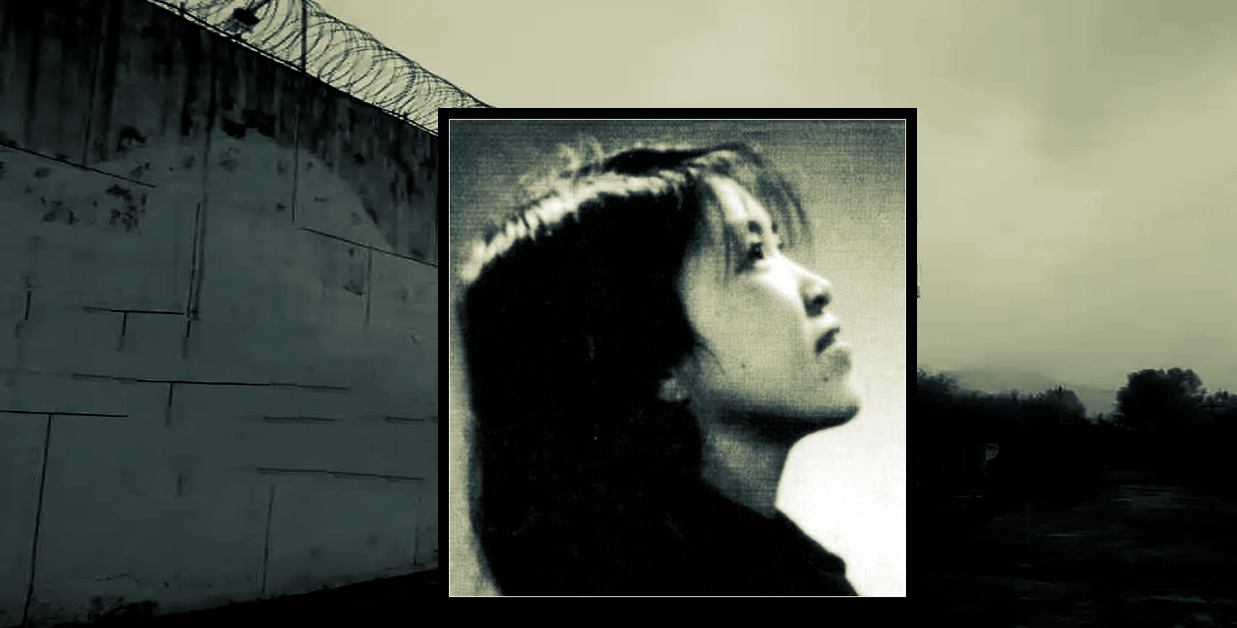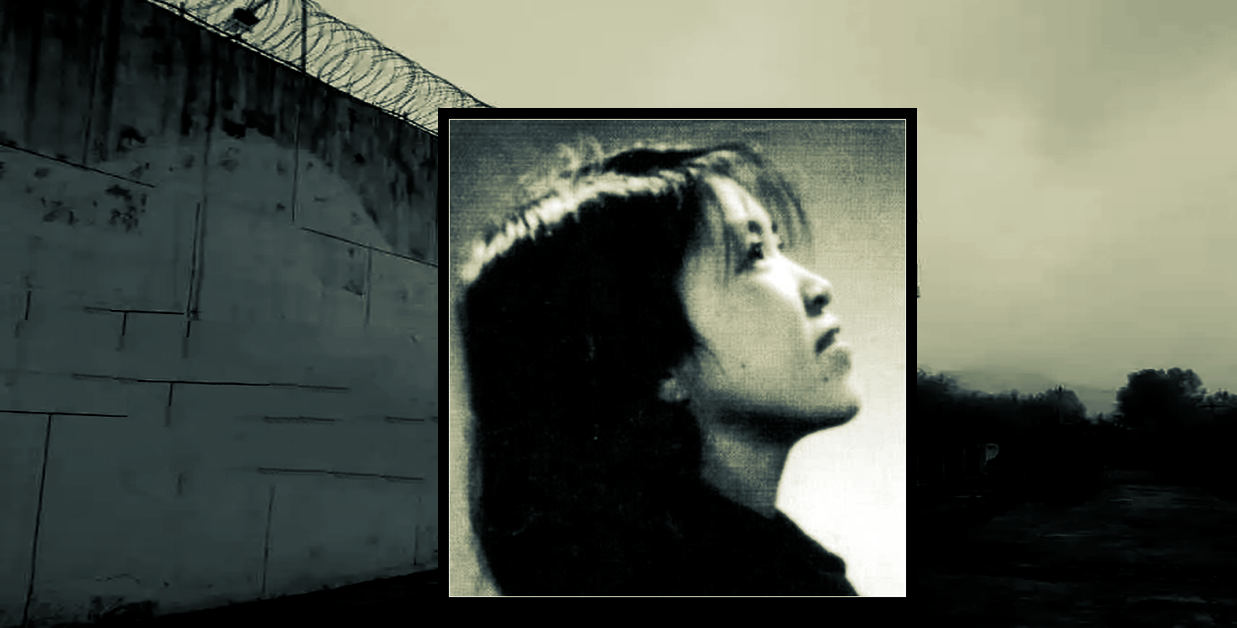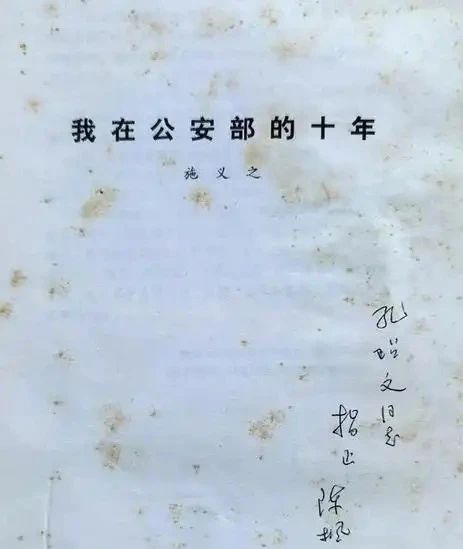秦暉,著名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曾任陜西師范大學教授、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本文來自2012年網易財經采訪。
這樣做是解決養老問題的前提
網易財經:近期看到有一些報道就說養老金已經出現了危機,現在是存在18萬億的漏洞,您是怎么看待這個養老金問題的?
秦暉:我覺得和養老金制度本身有關系的很可能就是我們的人口結構的變化。就是所謂的“未富先老”問題。而這個又是和另一項公共決策,就是計hua生yu制度是非常之有關的。
中國實行了三十幾年的獨sheng子nv政策,造成大量的所謂“一二四家庭”。這個事情從總體上來講,的確是會給國家的養老問題帶來很大的壓力。
而且我想,這個壓力其實還不僅限于這個政府養老金的壓力,實際上是整個社會造成的壓力。
因為即使你說國家不搞養老金了,讓個人養老,那個人也養不起。
這種“一二四家庭”大量存在的話,怎么可能養得起?
所以這個事情說穿了還是一個公共決策的問題:就是由于中國在非憲政民主制度下,很多公共決策,包括要公眾付出和給公眾多少回饋,在這兩個方面都有高度的缺陷。
所以養老金問題,我覺得只是這些缺陷那個的一個表現而已。
網易財經:您剛才提到一個就是公共付出和回報不成比例的問題,我們看到養老金的繳費和它的享受其實也是不匹配的。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有的人繳費多,但是他享受不了。
秦暉:關于這個問題,我覺得養老金的付出和匹配,如果要完全一致,那就是商業性養老。
比如說像保險公司交養老金,那你交多少,你就享受多少。
但是政府辦的養老金,或多或少都帶有轉移支付的功能。所以交的多,享受的多;交的少,享受的少,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講的。
但我們不能說,如果是這樣,那就有的人狂交,有的人不交就是合理的。
當然這個轉移支付要有一定的幅度,比如說在很多國家,養老金的支付都是三方支付,三方統籌的,就是國家、企業、個人都交一點。而且個人如果是窮人的話,他是可以免交的。
那么當然就會有你剛才講的這個問題,他既然不交,怎么還可以享受養老呢?我覺得這個道理很簡單嘛,福利就是要不讓人餓死的嘛,這是最簡單的。
但是這個東西當然它有個限度問題,如果你是個窮人,那么依靠社會保障體系能夠保障你的一些基本需求。但是這當然只是基本需求了。
所以在一般的發達國家,那個養老也有商業和福利這兩塊,其實醫療、教育都一樣。
我覺得整個福利制度就應該是這樣的,就是說窮人不應該失去保障,但是他也不能太奢侈。而富人如果你要更多的保障,那么你當然有商業這一塊做彌補,就像教育一樣,窮人可以上公立學校,但是富人你有錢,你上貴族學校嘛。
醫療也是一樣,窮人可以有醫院可上,但是最好的醫院可能都是私立的。
這和中國正好是相反的,中國的私立醫院凈是那種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那種便宜醫院,好醫院反而都是公立的,我覺得這個是非常荒誕的一種現象。
網易財經:您覺得應該怎么樣解決中國的養老問題呢?是解散養老金更好,讓養老金個人化,還是繼續維持養老金的體制呢?
秦暉:養老問題,其實我覺得它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你不能讓一些弱勢者就養不起老,或者說他就不應該活到老,或者他就,反正你不應該沒有人管。
但是管到什么程度這當然是一個問題了。
這種最基本的養老保險,應該不應該個人化是一個問題。即使是個人化,現在西方有一種思想,就是那種福利基金應該讓個人有更多的支配權。
比如說福利賬戶應該完全由個人可以使用,或者說可以進行經營,但是這和轉移支付的存在與否這還是兩回事。
就像現在在醫療和衛生這兩方面,西方很多國家都提出,說是政府辦的這種東西有很大的弊病,那你提供可以都是商業化提供。
但是有的時候支付能力國家還是要幫助的,比如說很多國家現在都提出用教育券來取代公辦學校,用醫療券來取代公立醫院,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就是說所有的醫院,所有的教育都可以市場提供,而且這個有競爭,就可以辦得好嘛,但是窮人上不起怎么辦,國家給他買單。
買單后你怕他喝酒了怎么辦?你怕他拿去亂花了怎么辦?你就不給現金,用代金券的形式來支付,這個東西你就把更多的權力就交給了個人。
比如說你只給他發教育券,他上哪所學校他就有選擇權了。
哪怕就是窮人也有選擇權,因為現在如果是公辦教育,如果你是只能上公立學校,那他只能就近入學,沒有選擇的。
但是如果你學校都是私營的,給窮人發教育券,窮人拿著這個教育券他就可以有選擇。
醫院也是一樣,其實養老也有這個問題。養老賬戶個人自主權的適當提高,我覺得這是可以考慮的,但是這個轉移支付的存在,恐怕還是難免的。
你不能說國家完全不管,就讓這個窮人或者沒有子女的人就餓死,那怎么可能呢?
何況在中國尤其不行。因為是中國進行強制性的政府干預,使得很多人就沒有后代,使得養兒防老的那種機制就被認為破壞了。
你這個搞了三十年的獨sheng子nv政策,使得很多人沒法兒養老,然后你說不管了,讓這些人自己(解決養老問題),那怎么可能呢?
這個養老金這個問題,我覺得現在就有推卸責任的趨勢,我是非常反對的。
具體的講,如果要國家想用強制性的推遲退休年齡來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我肯定是反對的。這個退休年齡不是不能推遲,但是你必須是自愿的。
而且有人說這個推遲退休年齡有可能導致兩個后果,就是對一些當官的,延長了他貪污的時間,延長他用權力撈錢的時間;對于那些不當官的,等于是減少國家對他承擔的責任,這當然是不公平的。
而且最簡單的一個說法就是,我們現在說養老金有這么大的虧空,這本來就是應該推進財政公開的一個最有力的壓力。
為什么我們不在這個方面施加壓力,反而讓老百姓無條件的就是接受這個統治者的推卸責任的說辭呢?
既然是這樣,你就要向我們亮賬目啊,你說那么大的虧空你都不向我們亮賬目怎么能行呢?你到底收了多少錢,拿去干什么去了?這個養老金這個收了以后,你的財政運作機制又是干什么了,是不是拿去買股票了,或者拿去搞了四萬億了,搞了什么十八萬億了,或者拿去修高速公路。
反正這些東西你都得給我們一個交代嘛,到底怎么回事。
所有的這些我們都不清楚,你就說哎呀,就是國家不負責你們養老了,你們就繼續干,哪能這樣蠻不講理呢?
我們可以用它來推動財政公開、預算透明,推動中國的其他領域的配套改革。
因為中國的養老金問題不是一個純粹的養老金的問題,它還涉及到,包括也非常直接的一點就是涉及到我們現在的人口政策,這個政策你不解決怎么能行呢?
老實說,如果獨sheng子nv政策這么一直下去的話,你就是延長退休也不解決問題,你最后就會導致這個整個這個社會的不可持續。
全球化導致歐元區的財政透支
網易財經:您在一些講座中提出用您的低人權框架去分析了歐洲的福利危機,和低人權優勢國家之間的關系,能否請您在這里給網友介紹一下?
秦暉:這個我講的比較多。講得簡單點就是人們需要統zhi者,是因為他們需要統zhi者提供公共服務。
你既然需要這種服務,你就應該讓步一些權力,反映在經濟上就是讓他征稅。
那么到底讓他多一點權力,多一點責任,還是少一點權力,少一點責任,這就成為一種談判的機制。
而且老百姓中首先你是要談判的,因為老百姓中就這個問題達不成一致的,肯定有些人愿意權大責也大的政府,有些人就愿意權小責也小的政府,那么最后怎么決定?當然最后就是多數決定了。
但是在正常情況下,不管是福利國家還是自由放任,都不會造成無限制的赤字的。
因為道理很簡單,在一個國家內,要么高稅收高福利,要么低稅收低福利。
你不能既低稅收又高福利,你不可能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
所以在正常情況下不會有這個問題,一旦選民做了這種荒誕的決策,他馬上就會受到報應,受到報應他就會改了。
民主制度下老百姓降低福利,或者增加稅收,都有的,老百姓都愿意,只要做得透明。
但是在全球化了以后,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會有一種透支功能,這種透支功能就會使選民容易做出那種不當的決策。
而且這種不當的決策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就會在很長的時間沒辦法糾正,因為他不斷地透支,老百姓沒有感到什么不能持續的問題。
既然是這樣,那誰都不愿意交稅,誰也愿意享受福利,那就會出現左右兩派共同造成一個大窟窿。
就是左派上臺就增加福利,但是征稅很困難,右派上臺,他就減福利,但是減福利很困難,那你這種一反一復,那就出現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出現的問題是因為透支,透支不是搶錢,透支是借錢,誰愿意被他透呢?
被他透有兩種人,有兩種機制。
一種機制就是現在歐盟這種機制。
這種貨幣一體化,但是財政并不一體化,國家還是一個個的主權國家。但是搞了一個歐元這么個統一的貨幣,你一個國家亂來,就可能把這個貨幣搞垮,那其他國家就得救你。
現在希臘在透支整個歐洲,就是這樣一種現象。
還有一種情況,那就是透支低人權國家。
你看低人權國家正好相反,左派政策一左就拼命收錢,但是就不給你花;政策一右,他就不給你花,但是他照樣向你收錢。那么像這種體制下的老百姓肯定消費很低,生產肯定過剩。
而且國家手中肯定有大量的錢,不管是通過貿易逆差還是通過國家購買國債,實際上都是供這些民主國家透支,當然就構成了這樣一種機制。
網易財經:如果沒有低人權優勢國家的興起,歐洲福利問題還會發生嗎?
秦暉:我們要講清楚,債務問題和福利問題是有關系的,但不是一回事。
我完全理解很多自由主義者對福利國家的批評,比如說高稅收,高福利會影響資本積累啦,會使人變得不思進取等等等等。
但是如果僅僅是這樣,和現在歐洲發生的事不是一回事的。現在歐洲人很多人其實是這樣,你要說這個高福利會導致GDP增長的慢,或者說這個經濟就停滯了。
他們認為我們發展到這一步已經夠了,我們何必要疲于奔命呢?活得瀟灑一點不行嗎?這個是可以的,而且說實在的,人類的發展的境界,也不見得就是一定要比賽GDP。
一種高水平均衡狀態下的,人們比較舒適的生存狀態,我覺得其實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種理想,我認為至少它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問題是,你不能靠透支來實現這一點。
而且我們現存的,不管是凱恩斯主義理論也好,是福利國家的那些理論家也好,他們也都沒有把他們的理論建立在無限透支的基礎上。
所以反對無限透支并不等于反對福利國家,你理解這個意思吧?
反對無限透支,就是說你不能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稅收和福利不搭配,使得這個國家就是無限制的就透支下去。這種無限制透支的這種狀況是無論福利國家理論還是自由放任理論都不能允許的,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大家都知道希臘在納稅上是非常之差的,那基本上是個典型的既低稅收又高福利的體制。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當然是不行。
你這個做法也不是福利國家的做法,如果是福利國家的做法的話,那這個稅收會收的希臘人受不了。
希臘人之所以現在這個樣子,也是因為他自己感覺不錯嘛,交的稅又不多,享受的福利又高,如果你真的完全不許他透支,一切的稅收都讓他出,那他也不至于被慣到現在這個地步。
網易財經:您主張西方福利國家向對外投資征稅,雙重征稅是否有利于減緩福利危機?
秦暉:雙重征稅不會減少福利國家的毛病,因為它本身就是高福利制度的一個體現。
高稅收、高福利,但是至少它能使福利國家延續下去。
至于你說福利國家本身延續下去是好是壞,這當然各人有個人的觀點。
持自由放任思想的人恨不得福利國家明天就垮掉,那他當然認為這就是不好的。
但我覺得,你至少對于贊成福利國家的人來講,你福利國家要在收支平衡,或者大體平衡的情況下能延續下去,那當然要多收點稅你才能延續下去。那就是很簡單的道理。
假如你又不收稅,又要搞福利,那你就不是個解決福利國家的問題。
而是整個國家就要崩潰了,或者說,它就會導致債務危機的惡化。
我剛才講的這個雙重征稅,它是指能夠減緩債務危機,同時使得福利國家能夠有一定的延續下去的那種。有利于它延續下去的因素,至于延續下去好不好,這當然是另外一個話題。
網易財經:您認為這些福利國家如何才能既是維持一個高福利的狀態,又能保持一個經濟活力較好的狀態?
秦暉:其實在全球化以前,這基本上是不成什么問題的。
因為一個憲zheng體制就是讓老百姓在這兩者之間反反復復的試。
老百姓選了個自由黨,結果經濟很活躍,投資也很旺盛,但是兩極分化很大。而且除了兩極分化很大以外還可能產生的一個問題,至少按照有一種學派的觀點,也認為就是投資的擴張,生產的擴大會造成生產過剩等等。
到了適當的時期,老百姓就會做一個相反的選擇,就選一個左派去改變一下這種狀況。但是左派也有它的問題,這個問題老百姓不是感覺不到的,比如說動力就少了。
除了動力少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稅收多了,投資率就低,投資率低的話,老百姓就業也可能會產生問題。
那么老百姓感到這個問題,他們下一輪就又會投右派的票,或者老百姓也不滿意賦稅重,那么右派說它可以減稅,那下一次老百姓就又選右派。
這個問題我覺得,在一國的憲zheng體制下,如果我們把經濟的范圍放在一個國家內的話,一般來講憲zheng民zhu體制會調整到一個大家都認為是適中的這樣一個程度。
但是現在全球化以后,就會造成這種機制就很難運行下去。
網易財經: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造成了您說的這個調節機制的一個失效,在這種全球化的情況下,有沒有一個較好的辦法平衡?
秦暉:這就是我講的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你現在有了全球市場,有了全球投資,甚至還有了全球融資這樣一個平臺,但是如果你沒有一種基本的全球公認的人權標準,全球公認的一個憲政制度,甚至我講的更極端一點,如果你要用共同貨幣的話,還有一個同的主權的問題,就像希臘和歐洲面臨的那樣,如果是這樣你肯定要垮掉的。
現在歐洲就是如此,主權一體化你不邁進,那貨幣一體化就得垮。
在全球也是一樣,如果你這個人權的全球化過程如果不能跟上的話,那你這個單一的經濟全球化過程,就肯定是要受到阻礙,甚至要倒退的。
我不是用所謂的昂納克預言這個概念講過嗎?如果你是這樣搞的話,那你東德拆掉了柏林墻,西德還得把它樹起來,否則的話東德就被西德搞垮了。
網易財經:您多次提到民主具有一個糾錯的功能,我們之前采訪過經濟學家許小年老師,他提出說,民主提出了糾錯的可能,但不是必然糾錯,您怎么評價他的這個觀點?
秦暉:他這個觀點當然是很對的。
首先我們講,民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每次決策都是對的,民主制度下肯定會有不斷犯錯誤的。
但是我們平時講的比較正常的,就是民zhu政治不應該犯太大的錯誤,或者尤其是它不應該犯持續性的錯誤。
比如說不管是減稅減得太多,還是福利搞得太大,都會造成窟窿,到了一定程度,民主制度都可以糾正這個做法的,但是那是在以前。
現在出現的一個問題,我覺得我比許小年更為悲觀的一點就是,如果目前的這種機制不改變的話,民主制度是沒有糾錯功能的。
在這個問題上,他一定要把這個窟窿,要把這個債務陷阱搞到最后包不住了,全球垮臺,那種情況它才能夠收手,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我最近寫的一篇文章叫做《憲zheng民主遭遇全球化》嘛,指的就是這個問題。所以這個全球化的確是使一國之內憲zheng民主的糾錯機制出現非常嚴重的問題。
現在甚至不是許小年講的那種,它不一定能夠糾錯的問題,而是它幾乎一定不能糾錯的問題。往往要讓那個錯誤犯得很大。
解決這個問題有兩個辦法,一個就是把他們的民主也搞垮掉,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讓其他地方也民主起來。
我們當然是希望其他地方也民主起來。總之,我們總是希望良幣驅逐劣幣,而不是劣幣驅逐良幣。
網易財經:您剛才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您認為的解決方法,就是說全球首先要對人權有一個基本的共識。
秦暉:對。
網易財經:再次就是全球化還需要一些什么?
秦暉:咱們經濟全球化和其他方面的治理全球化,其進展必須適應。這兩者的脫節不能太厲害。
當然你這個經濟一體化程度越高,你對政治一體化程度提出的訴求當然也是越高。
因為希臘已經加入了歐元區了,那么它當然對歐洲政治一體化的要求就會更高了。
比如說歐洲要采取措施,向歐洲合眾國方向發展,當然不一定能夠一步發展到,但至少你在財政上要約束各國的財政主權。
不能像希臘這么無限的透支下去,《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本來也已經有了約束了,但是他們不接受。不接受還是因為你這個政治上沒有建立這個機制。
但是對于中國來講,當然中國也沒有加入什么歐元區,中國現在也沒有在用美元,我們可以說,全球所謂的在政治上的全球化可能不至于要走到什么全球合眾國的地步。
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也不可設想,但是中國提高人權水平,提高公眾的福利問責能力和權力限制能力都是非常必要的。
希臘是個自私的國家
網易財經:您剛才提出的就是希臘危機,有可能會造成全球性的崩潰,這個是您對希臘危機做的一個預測?
秦暉:其實這個歐債危機是一步一步拖到現在的。
其實即使在希臘大選前,我都認為希臘要退歐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其實擺在希臘面前的兩條道路都是可以走的,要么緊縮,要么退歐。
你要么還想待在歐元區,就通過緊縮,自己約束一下自己;要么你不愿意干,你就退歐了,我覺得無論兩種辦法的哪一種,早做都比晚做要好。
它退歐當然會對全世界,尤其是對歐洲造成很大的沖擊。
因為希臘已經欠了很多的錢,如果它一不還,一賴賬,那會使它欠錢的人發生資金斷裂類的問題。
但是因為希臘這個國家畢竟很小,它就是發生這種問題,歐洲那幾個主要的國家是完全可以應付的。
這么做會對希臘造成什么后果呢?無非就是希臘那個貨幣一下子貶值貶得不象話,因為它要靠自己印錢來填補這個窟窿。
希臘人的那個工資都一下降到很低,那這個說實在的,如果我們相信市場機制的話,肯定會在低水平條件下找到個平衡。
希臘變得工資很低了,那人家就愿意去投資了。
大家都知道現在土耳其的勞工遍及世界,歐洲大量的資本向土耳其轉移,不向希臘轉移,原因就是因為希臘人的工資特高。
你如果低了,那這些投資就向希臘轉移了,就不用向土耳其轉移了,那希臘的制造業就可以興起來,希臘的經濟就可以有一個復蘇的起點。
何況我一直覺得,希臘在歐盟和歐元區內,這十多年來它的作用一直是很不好的。
因為在很多問題上希臘都顯得非常自私,比如說在土耳其入歐這個問題上,希臘是非常反對的。
因為希臘在歷史上跟土耳其是世仇,而且東正教和穆si林的關系也都特別緊張。
當然,這個歐盟有一個一票否決的機制,它只要有一個不同意,你就不行。
很多歐盟和土耳其的很多那種協議就是因為希臘不贊成就黃掉了。
比如說還有一個,就像解決馬其頓問題什么的,也是其他國家都同意的,就是希臘不干,而且希臘不干的原因就是完全是很自私的。
比如說它和馬其頓的關系,它就認為馬其頓這個國家不存在。因為它理解的馬其頓是希臘北部的地方,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它就不同意歐盟和馬其頓發生關系。
我覺得如果要從歐盟的這個大框架來講的話,土耳其現在比希臘更有資格待在歐盟里頭,希臘的退出沒準兒會使歐盟減少很多麻煩,而且使得歐盟會有生機。
但現在最糟糕的問題就是,包括希臘這次大選,就是希臘人還是表示要待在歐元區里頭。
但是它還是不愿意緊縮,還是這么拖下去,我覺得越拖下去這個問題就會越嚴重。
你早點解決,你不管采取什么方式解決,都比這種要好,最后其實他們還是得解決的。
我覺得希臘的前景到現在無非是,要么緊縮,要么退歐,沒有其他的選擇的。
但是就是你早點選擇要比你不死不活的一直拖下去要強得多。
網易財經:在低人權優勢之外,您認為中國有沒有比西方做得更好的地方?
秦暉:你要說它的某一次決策,民zhu制度從來沒有保證它每一次決策都比專zhi國家要更機靈。
更何況其實從體制來講,民主國家的一個特點就是,它的決策過程比較復雜,好處就是那個壞決策很難通得過。
壞處就是好決策也不一定很容易通得過。
所以就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是沒有什么問題的,專zhi者完全可以做出比民主國家聰明的決策,但是這并不說明專zhi制度比民主zhi度更可取。就是不排除他有可能做出這樣的決策。
在體制上中國肯定是要向西方學習的,我這里講的是整體上的西方,不是指的某一個國家,比如說西方有某些國家可能是有很大的問題。
政府的權與責應相對應
網易財經:中國改革已經三十年,有沒有正式或者非正式的體制在未來的制度演進中應該是著力保留下來的?
秦暉:我覺得制度演進從來就是漸進的,至少是我希望它是漸進的。當然也有那種突變的,發生劇烈革命,推倒重來的。
但至少我是希望它是漸進的,既然我是希望它是漸進的,那肯定是不存在著沒有什么不能保留下來的問題。
但是什么都得發生改變,我講的這個改變就是指的通過漸變來走向這個方向。比如說就是我剛才講的這兩個方向,福利問責要逐漸的加大,以前統zhi者給你一點你就得感謝皇恩浩蕩,不給你也不能要。
現在大家就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你給我我也不感謝,你不給我我就會問責,這個也是逐漸在加強。
你也不能說是把什么破壞了,然后才能有這個東西。這個訴求也是在不斷地提高的。
還有限權也是這樣,我們的統zhi者的權力以前是完全不受制約的,現在逐漸逐漸變得受制約,以后將會越來越變得受制約,這個過程也應該是漸進的。
所以無論是在權力體制上,還是責任體制上,中國都沒有。
當然如果你不改,那在危機積累起來以后,這個變革可能就會變得比較突兀。
如果中國能夠向漸進的方向發展,尤其是能夠在限權和問責這兩個方面不斷取得進步的話,那么這個變化將會比較連續,將會比較漸進。
就不存在著什么需要一股腦的拋棄這樣的問題。
網易財經:在您的演講中,您提到說建設民主she會主義,您現在怎么看自己,您自認為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還是一個民主she會主義者呢?
秦暉:這個事情我說過無數次了。我覺得這個東西在前憲Zheng條件下,就根本就沒有區別。
就限權問責這兩個我都是主張的,就我主張問責而言,我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就我主張限權而言,我就是自由主義者,這有什么矛盾。
只有在憲Zheng條件下這兩者才是矛盾的,因為當你面臨著權大責也大的國家,和權小責也小的國家的時候,那么你當然你選權小責也小的國家,你就成為狹義的自由主義者。
當然這個自由主義也有各種各樣的理解,最狹義的尤其是從經濟上理解的所謂的自由放任主義者。
他當然就是主張權小責也小的,那個社會min主主義者當然就是贊成權大責也大的。
但是在我們這樣一個權力無窮大,責任幾乎沒有,我這里講的幾乎沒有是指它必須承擔的責任它幾乎沒有,而不是說他不做事。
早就有人說我們的政府做了無窮的事,那是你愛做的,不是老百姓可以逼你做的,你做了事是你的恩情,你不做我也不能跟你要,那不能叫責任的。
老百姓是主人要讓你做的事,這才是責任的,這種事情其實很少的。
像養老這都是這樣的,政府給你做一點是可以。
它想不做它就不做了,那是不行的。
那么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不僅是我,我認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在這兩個方面做努力,比如說假定我是一個自由放任主義者,我是弗里德曼那樣的人,我在美國我可以反對福利國家。
尤其是我絕對不能贊成從搖籃到墳墓都由國家來承擔責任。但是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句話,權力沒有邊界,你責任就不應該有邊界,這個責任就要大到你告饒為止。
你想不承擔這個責任,那你就約束你的權力,憲zheng就這么來了,就這么簡單。
我這里講的是經濟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在憲zheng國家意味著反對福利國家,意味著主張權力小,責任也小的國家。
但是不管任何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在非憲zheng體制下,都意味著他是在推動憲zheng,不管是從限權的角度,還是從問責的角度。
Read/Ed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