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把兒子送到美國以后……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高鋼做訪美學者時,將他9歲的兒子送進了美國學校,沒想到美國的教育是這樣的……
當我把九歲的兒子帶到美國,送他進那所離公寓不遠的美國小學的時候。
我就像是把自己最心愛的東西交給了一個我并不信任的人去保管,終日憂心忡忡,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學校啊!
學生可以在課堂上放聲大笑,每天至少讓學生玩兩個小時,下午不到三點就放學回家,最讓我大開眼界的是沒有教科書。
那個金發碧眼的美國女教師看見了我兒子帶去的中國小學四年級課本后,溫文爾雅地說:
“我可以告訴你,六年級以前,他的數學不用學了!”
面對她充滿善意的笑臉,我就像挨了一悶棍。
一時間,真懷疑把兒子帶到美國來是不是干了一生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看著兒子每天背著空空的書包興高采烈地去上學,我的心就止不住一片哀傷。
在中國,他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書包就滿滿的、沉沉的,從一年級到四年級換了三個書包,一個比一個大,讓人感到“知識”的重量在增加。
而在美國,他沒了負擔。這!能叫上學嗎?
一個學期過去了,把兒子叫到面前,問他美國學校給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著用英語說:“自由!”
這兩個字像磚頭一樣拍在我的腦門上。
此時,真是一片深情懷念中國教育。
 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為什么中國孩子老是能在國際上拿奧林匹克學習競賽的金牌。
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為什么中國孩子老是能在國際上拿奧林匹克學習競賽的金牌。不過,事已至此,也只能聽天由命。
不知不覺一年過去了,兒子的英語長進不少,放學之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圖書館,不時就背回一大書包的書來。
問他一次借這么多書干什么,他一邊看著借來的書一邊打著電腦,頭也不抬地說:“作業。”
這叫作業嗎?
一看孩子打在電腦螢幕上的標題,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中國的昨天和今天》。
這樣大的題目,即使是博士,敢去做嗎?
于是我嚴聲厲色地問是誰的主意,兒子坦然相告:老師說美國是移民國家,讓每個同學寫一篇介紹自己祖先生活的國度的文章。
要求概括這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文化,分析它與美國的不同,說明自己的看法。
我聽了,連嘆息的力氣也沒有了,我真不知道讓一個十歲的孩子去做這樣一個連成年人也未必能做的工程,會是一種什么結果?
只覺得一個十歲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以后恐怕是連吃飯的本事也沒有了。
過了幾天,兒子就完成了這篇作業。

沒想到,打印出來的是一本二十多頁的小冊子,從九曲黃河到象形文字,從絲路到五星紅旗……熱熱鬧鬧。
我沒贊成,也沒批評,因為我自己有點發愣。
一是因為我看見兒子把這篇文章分出了章與節,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參考書目。
我想,這是我讀研究生之后才運用的寫作方式,那時,我三十歲。
不久,兒子的另一篇作文又出來了,這次是《我怎么看人類文化》。
如果說上次的作業還有范圍可循,這次真可謂不著邊際了。

兒子真誠地問我:“餃子是文化嗎?”
為了不耽誤后代,我只好和兒子一起查閱權威的工具書。
費了一番氣力,我們完成了從抽象到具體又從具體到抽象的反反復復,兒子又是幾個晚上坐在電腦前煞有介事地作文章。
我看他那專心致志的樣子,不禁心中苦笑,一個小學生,怎么去理解“文化”這個內涵無限豐富而外延又無法確定的概念呢?
但愿對“吃“興趣無窮的兒子別在餃子、包子上大作文章。
在美國教育中已經變得無拘無束的兒子無疑是把文章作出來了,這次打印出來的是十頁,又是自己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著一本本的參考書。

他洋洋得意地對我說:“你說什么是文化?其實超簡單——就是人創造出來讓人享受的一切。”
那自信的樣子,似乎發現了別人沒能發現的真理。
后來,孩子把老師看過的作業帶回來,上面有老師的批語:
“我安排本次作業的初衷是讓孩子們開闊眼界,活躍思維。而讀他們作業的結果,往往是我進入了我希望孩子們進入的境界。”
問兒子這批語是什么意思,兒子說,老師沒為我們感到驕傲,但是她為我們感到震驚。
“是不是?”兒子問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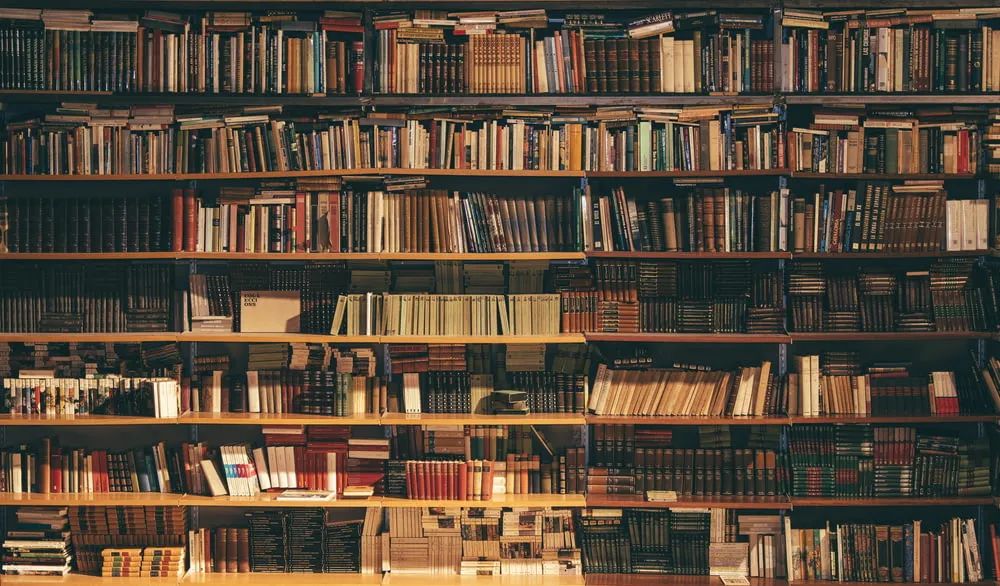
我無言以對,我覺得這孩子怎么一下子懂了這么多事?
再一想,也難怪,連文章題目都敢作的孩子,還有什么不敢斷言的事嗎?
兒子六年級快結束時,老師留給他們的作業是一串關于“二次世界大戰”的問題。
“你認為誰對這場戰爭負有責任?”
“你認為納粹德國失敗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是杜魯門總統的高級顧問,你將對美國投原子彈持什么態度?”
“你是否認為當時只有投放原子彈一個辦法去結束戰爭?”
“你認為今天避免戰爭的最好辦法是什么?”

如果是兩年前,見到這種問題,我肯定會抱怨:這哪是作業,分明是競選參議員的前期訓練!
而此時,我已經能平心靜氣地循思其中的道理了。
學校和老師正是在這一個個設問之中,向孩子們傳輸一種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引導孩子們去關注人類的命運,讓孩子們學習思考重大問題的方法。
這些問題在課堂上都沒有標準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們用一生去尋索。

看著十二歲的兒子為完成這些作業興致勃勃地看書查資料的樣子,我不禁想起當年我學二戰史的樣子,按照年代、歷史事件死記硬背!
書中的結論明知迂腐也當成《圣經》去記,不然,怎么通過考試去奔光明前程呢?
此時我在想,我們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重復前人的結論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
而沒有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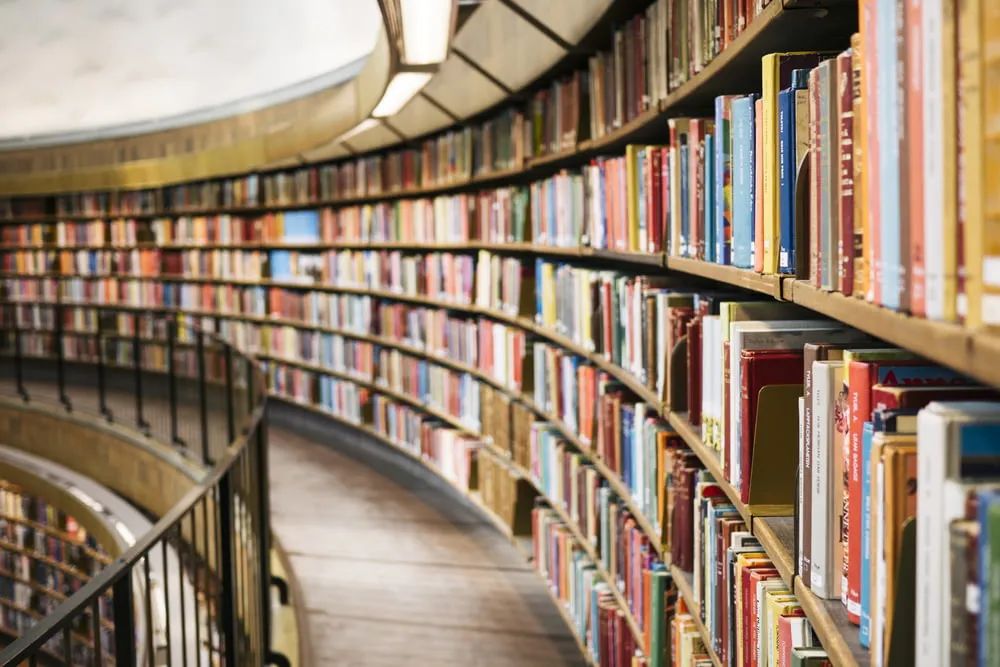 己的思考,就難有新的創造。
己的思考,就難有新的創造。 兒子小學畢業的時候,已經能夠熟練地在圖書館利用電腦和微縮膠片系統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種文字和圖像資料了。
有一天,我們倆為獅子和豹子覓食習性爭論起來。
第二天,他就從圖書館借來了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拍攝的介紹這種動物的錄影帶,拉著我一邊看,一邊討論。
孩子面對他不懂的東西,已經知道到哪里去尋找答案了。
兒子的變化促使我重新去看美國的小學教育。

我發現,美國的小學雖然沒有在課堂上對孩子們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
但是他們想方設法把孩子的目光引向校外那個無邊無際的知識海洋。
他們要讓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時間和空間都是他們學習的課堂,他們沒有讓孩子去死記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
但是,他們煞費苦心地告訴孩子怎樣去思考問題,教給孩子們面對陌生領域尋找答案的方法。
他們從不用考試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盡全力去肯定孩子們一切努力。
去贊揚孩子們自己思考的一切結論,去保護和激勵孩子們所有的創作欲望和嘗試。

有一次,我問兒子的老師:“你們怎么不讓孩子背記一些重要的東西呢?”
老師笑著說:“對人的創造能力來說,有兩個東西比死記硬背更重要:
一個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尋找所需要的比它能夠記憶的多得多的知識;再一個是他綜合使用這些知識進行新的創造的能力。
死記硬背,就不會讓一個人知識豐富,也不會讓一個人變得聰明,這就是我的觀點。”
我不禁想起我的一個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談話。

他學的是天文學,從走進美國大學研究所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學位的整整五年,他一直以優異的成績享受系里提供的優厚獎學金。
他曾對我說:“我覺得很奇怪,要是憑課堂上的學習成績拿獎學金,美國人常常不是中國人的對手。
可是一到實踐領域,搞點研究性題目,中國學生往往沒有美國學生那么機靈,那么富有創造性。”
我想,他的感受可能正是兩種不同的基礎教育體系所造成的人之間的差異。
中國人太習慣于在一個劃定的框子里去施展拳腳了,一旦失去了常規的參照,對不少中國人來說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慌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國的小學教育,想到那些課堂上雙手背后坐得筆直的孩子們,想到那些沉重的課程、繁多的作業、嚴格的考試……
它讓人感到一種神圣與威嚴的同時,也讓人感到巨大的壓抑和束縛,但是多少代人都順從著它的意志,把它視為一種改變命運的出路。
這是一種文化的延續,它或許有著自身的輝煌,但是面對需要每個人發揮創造力的信息社會。
面對明天的世界,我們又該怎樣審視這種孕育了我們自身的文明呢?
Read/Edit > -
我本被仇恨控制了,美國之行改變了我!

1
我兒時第一次關于仇恨的記憶,是六歲第一次見父親。
一個文化人,連林某的頭發絲都沒見到一根,莫名其妙就變成了林某集團的一員。
一番非人的折磨與拷打之后,想到自殺,正好母親生下我,托人帶信給他,才打消了自殺的念頭,從此被軟禁在貨船上撐船。
因為變態級仇恨的存在,一直不讓夫妻見面,不讓父子見面,直到我六歲那年,母親送了禮,在船經過家鄉時讓我上船見一下父親,并且不準許母親陪我上船,也不準父親下船。
讓父子見面已是天大的恩德,再讓夫妻見面,那就太沒有革命立場了。
記得那是一個愁云慘淡的冬天,我捧著一個和我上身一樣高的菜籃子,幾乎擋住了我的視線,菜籃子里放了幾根油條,慢慢走過船上的跳板。
船與岸之間的跳板很窄很長,河岸很高,一個六歲的孩子,不允許母親陪在身邊,我非常非常地害怕。
船上有很多看熱鬧的人,不僅沒一個人幫助一下六歲的小孩,沒有一絲悲憫,還粗俗地哄笑著讓我叫他們爸爸。六歲的孩子不知叫爸爸的含義,但能體會到他們的惡意,越發緊張起來。
我從沒見過父親,但一眼就認出了他,因為船上只有一個人淚流滿面,只有一個人眼里充滿著愛。
我走到他面前,把菜籃子遞給他,怯怯地說:爸爸吃油條。
父親一把抱住我,淚如雨下。
然而,這樣的場景下,不僅沒有一個人動容,一堆人還邊議論邊說臟話。
仇恨的種子開始在我幼小的心中發芽,我在船上待了一個下午,趁他們不注意,在他們喝水的茶缸中撒了一泡尿。
2
十五歲那年,我和一個女生戀愛了。
“奸情”敗露后,校長與教導主任道貌岸然地找我談話,一番大道理后,叫我交待“細節”比如如何解紐扣?如何接吻?先摸哪?后摸哪?怎么摸的?
然后不停地劃重點:細節細節!
沒有一絲人文關懷與同情,只有變態的偷窺欲,隨后就是讓我巡回作報告檢討認罪,在大庭廣眾的同學們面前,把我的“奸情”復述N遍。
由此我成了當地的“名人”。看著他們開心的樣子,當時我覺得,如果我能掌控這個世界,一定會將他們碎尸萬段,挫骨揚灰。
仇恨的種子,在心中壯大成長。
長期仇恨教育帶來的群體性后遺癥,就是只顧自己不顧別人,心中只有冷漠與自私,少有愛與憐憫,并且頭腦簡單極易被煽動,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毫不例外,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了仇恨愚昧大棋中的一顆棋子。
3
在我公司初創時期,員工們全年無休,每天加班到半夜。
一次朋友介紹一個人到我公司上班,半夜下車后直奔公司找對接人。他到公司時已是凌晨1點多,當看到滿屋的人都在加班,嚇得第二天就回去了。
在我的早期博客里,充滿了滿滿雞血的戾氣。錢是賺了一點,但總處于一種莫名緊張的壓迫感中,容易暴怒或情緒大起大落,沒有一點幸福感,直到有一年,我登上了去美國的飛機……
我是個對周邊環境特別敏感的人,只要去過一個地方,下次再去時,哪怕有一點輕微變化,我都能感覺出來異樣。
當我第一次踏上美國的達美航空,立即感覺怪怪的。
在我們的固化思維中,空姐們應該個個年輕貌美,身材苗條,但在達美航空,有慈祥的奶奶,也有憨憨的膀大腰圓的印度人。
在滿滿的疑惑中,那些空姐,哦不對,應該是空媽、空叔、空奶奶們開開心心地給我們送餐,服務。我能真實的感受到:她們的服務與微笑是發自內心的,而不是職業的。
很快,受到她們情緒的感染,我不知不覺地心情變得快樂起來。
到了美國,也很不適應,因為早上出門,不管認不認識的,都是很開心地與你打招呼,即便是路邊的流浪漢,也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快樂。
雖然美國也有很多問題并不完美,但在快樂上,與我們中國人的愁眉緊鎖、心思慎重完全不同。
直至回到中國,一直都沒能想明白,為什么這些人會這么快樂?為什么美國人不加班,并且以我們的觀點來看:他們這么懶,卻創造了接近全世界40%的GDP?
帶著滿滿的疑惑,來來回回在中美之間走了N回,終于明白了:
在美國,不可以有職業歧視,不能因為身材原因不能讓人當空姐,否則就是違法。
在美國的立國之本中,人人生而平等,你有錢,我羨慕,但不代表我低你一等。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也擁有足夠的尊重,并且是發自內心的、不是嗟來之食式的尊重。
其中最典型的是小費。我一直覺得小費好麻煩,不愿給,后來終于悟到,小費是給弱勢群體一個體面增加收入的方法。你付出幾美元,不會因此而破產,而弱勢群體每天都能不斷收到心安理得的小費,收入就會大增。
人人心中有愛,人人得到平等的尊重,人人都會付出愛,就會發自內心地快樂,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4
最著名的大事件,莫過于兩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后,英法聯軍對德國進行了懲罰式壓榨,用仇恨去對付仇恨,恨出了一個希特勒,引發了更大的災難。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吸取了教訓,不僅沒對戰敗國進行壓榨,還提供了著名的馬歇爾計劃,主動倒貼錢幫助戰敗國進行戰后重建,得到了戰敗國發自內心的感激,也贏得了長久的和平與繁榮。
這個世界,最強大的力量并不是槍炮,而是愛!
在這之前,我對員工與弱勢群體也是漠視且不尊重的。
比如,我曾說過不要拖家帶口的員工,對寫字樓保潔員視而不見,甚至會跟路邊停車收費員爭執。我的心態始終是在驅使、在漠視這個世界。
在這種情況下,得到的也是驅使,也是漠視。不僅情緒容易大起大落,賺點錢,內心并不快樂,公司也沒有一種讓人安心穩定的核心競爭力,需要不停地驅使、施壓,才能有所推動,弄得身心俱疲。
受美國文化的影響,我開始學會尊重每一個人。
遇到保潔員我會問候,遇到停車收費員來不及過來收費,我會主動等候付費并多付一點。
一開始有點刻意,但時間長了,真正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快樂。
同時我開始盡最大可能不讓員工加班。以前員工生孩子我會“按章”扣除福利,現在不僅不會“按章”扣除,還會給予更多照顧。
我領悟到:對老板而言,生意是全世界,對媽媽而言,孩子是全世界。
每個人的理念、精力、家庭是不同的,不能以自己的工作能量與激情去要求每一個人。這個世界需要奔跑的人,也需要在路邊鼓掌的人。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生活理念與形式的權利,這是每個人的天賦權利。
作為一個相對強勢的老板,更要理解這種權利,發自內心地尊重員工,不要高高在上,人人都是平等的。
以前每每聽到什么企業文化、狼性文化,都覺得非常欣賞,但最近一次聽到華為的一個資深員工,因為老婆不愿去深圳,要辭職回北方,任正非就勸這個員工與老婆離婚。
我本來很敬重任正非,通過這件事改變了我的看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戀愛,要送孩子上學,要輔導孩子高考,要照顧父母,不可能也不應該把所有的時間都交給工作。
作為老板,壓力再大,委屈再多,都不應該讓員工放棄生活的快樂而完全地投入到工作中。
我真心這樣認為,也這樣做了。相反,公司并沒有因此而衰退,客戶并沒有因此而不滿,反而有一種無形的力量,使我們競爭力越來越強。
我自己心情越來越寧靜,再也沒有情緒大起大落或暴怒過,找到了自創業以來,從未有過的強大、篤定、自信與安寧。
5
這些年來,國民素質開始提高,很多人開始鄙視一些老人插隊爭搶的不文明行為。
老人們的不文明行為確實不值得提倡,但大家不知道,在他們那個年代,如果不爭不搶不插隊,孩子可能就沒有吃的,甚至會餓死。
他(她)們其實都是偉大的父親母親,真正要鄙視的不是他們的行為,而是把他們逼成那樣的人。
悟到了這個道理,我對兒時羞辱我的船員,偷窺隱私并侮辱我的校長與教導主任們一一釋懷了,我從內心真正原諒了他們,他們其實都是仇恨教育的犧牲品。
一位情感專家說得好:其實這個世界上并沒有潑婦,女人天生都是溫柔的,關鍵看她們遇到了什么樣的男人。這是同樣的道理。
非常羨慕“歲月靜好”這個詞,在一個最美的人間四月天,泡一壺清茶,與孩子以及愛人一起,看杏花微雨,聽風起鳥鳴,賞日出日落,聞暗香紛飛。
可是,當一切都充滿不確定,當一切都隨時有假,難辨真偽,當人們心中充滿愚昧與仇恨,即使有眼前美景,也難以有長久的歲月靜好。
每個不停輸出仇恨的人,表面上暫時有了快感,但最終仇恨會反噬他們,覆巢之下,沒有完卵。
上周出差,飛機遲遲不飛,一問是在等兩個海外轉機的孩子做檢測。
當兩個十六七歲的孩子上了飛機,乘客們開始高聲咒罵起來,一會罵孩子是千里投毒,一會咒罵空姐,要投訴要下飛機,誰也不肯孩子坐在他們身邊。兩孩子手足無措地哭了。
這讓我想起兒時那個冬日下午,六歲的我獨自一人走過又窄又高的跳板,去見六年不讓相見的父親;也想起了遠在美國的孩子,想到他也可能受到這種委屈,心中一酸。
雖然我也有些擔心,但還是忍不住招招手,叫他們坐在我身邊。孩子哭著說謝謝叔叔。
我內心很難受,這么多年過去了,經濟已今非昔比,但仇恨與自私卻一絲未減。
只論成敗不論對錯,只論立場不論人道,我們這些中流砥柱年齡的男人們,只顧追逐財富,沒能給孩子們一個充滿愛的世界,還在讓無休止的仇恨與自私代代相傳,導致我們的下一代,仍無法擁有一個歲月靜好的未來。
我告訴兩個孩子,不要謝我,只要記住不要學習那些人,也不要恨他們就行。他們也是多年仇恨教育的犧牲品,良知的光芒,暫時還沒有照亮到他們那被仇恨籠罩的暗黑的心靈。
在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不是恨,而是愛,仇恨能折斷路邊的野花,仇恨阻擋不了春天的到來!
Read/Edit > -
張維迎:中國數千年停滯不前,根在思想壟斷!
張維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此文為張維迎教授2014年8月在鳳凰財經“智友會”上的演講
本文轉自公號:思想堂
思想堂
思想薈萃
公眾號
首先謝謝智友會組織這樣一個讀書會。我先講幾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想談談啟蒙。啟蒙的本意就是原來生活在黑暗當中,我們看不見,我們在一種愚昧狀態當中生活。而啟蒙的核心就是“燈”,讓我們自己清醒,從愚昧當中解放出來。我們所謂的“愚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人究竟是什么。可以說,我認為現在大部分中國人,60%以上甚至于說99%,不把自己當人看。怎么不把自己當人看呢?人和動物之間最大的區別是什么?不是吃喝拉撒,吃喝拉撒這些方面動物都會有一般。生物性欲望的滿足方面人和動物是一樣的。能把人和動物區分開來的,其實就是我們的思考,我們的自由意志。這也是康德講的。
我們之所以是人,是因為我們有理性、能思考、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包括了要去表達。如果你想說一個話,別人不讓你說,你就不說了,這就是你不把自己當人看。啟蒙就是要認識人就是人,人之所以跟動物不一樣就是有自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只有有了自由,我們才活的有尊嚴。如果沒有自由,你就沒有尊嚴,這一點非常重要。
西方在幾百年前,尤其是十八世紀,無論是法國的啟蒙思想家,還是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或像德國康德這樣的人,他們做的就是這樣的工作,告訴人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權利,什么樣是有人的尊嚴。我們中國一直沒有經過這個階段,我們直到在一百多年前,特別是在甲午戰爭之后才認識到這個問題,所以開始了思想啟蒙。
但是這個思想啟蒙到了上世紀二十年代基本上就中斷了,被“一個主義”代替了中國人應有的啟蒙,然后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末期。改革開放以后好多思想界的人做了一些啟蒙性的工作,到1989年也中斷了。到現在仍然沒有經過真正的啟蒙,啟蒙在中國是一個“半拉子”工程,也就是一個“夾生飯”。中國人對基本的權利,對自由這些東西都是非常模糊的,也包括對民主的看法。自由是比民主更重要的東西。如果沒有自由的理念,那么我們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這是我談的第一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這本書里面已經多次講到了。我這幾年還有一個重要的認識,就是“理念、思想、觀念對人類的重要性”。人類的歷史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觀念歷史。所有人類的創新,甚至于物質上的合作其實都是從觀念變來的。我在這幾年對傳統講的歷史唯物主義產生疑問,因為歷史唯物主義沒有解決人類的很多問題。比如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會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這個東西是講不通的。我們看一下人類的歷史,其實你的生產力、技術很大程度上是由上層建筑來決定的,是由生產關系決定的。我們看一下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比較,最新一些技術的創新都出現在哪兒?出現在美國,而不是出現在中國。那么我們唯一能找到的理由就是我們的產權制度約束了人們創造的自由。
甚至從一般的技術來講,其實就是由一個想法導致的。如果沒有自由思考環境的話是不可能的。比如新的電動汽車特斯拉為什么在美國出現了,在中國為什么出現不了?在中國搞企業的人就會想這個事能不能去做,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規定?這些約束性就導致很難有創造性的思想,更不用說社會科學這個行業了。
自由就像空氣一樣。不是說搞社會科學的對這個敏感,搞自然科學的就不敏感。自由就像空氣,無論搞什么學科如果沒有自由空氣的話,人的思維本身就會僵化。
我在書里面談了好多例子,在這里我也不多講了。由于我是搞經濟學的,大家知道經濟學家談的都是利益。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人只受利益的驅動。我想這是一個悖論。按照經濟學傳統假設的話,經濟學家說什么與人們的行為沒有關系,因為人們最大化自己的效益、利潤。無論經濟學家主張什么觀點,人家知道自己怎么做,該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有沒有經濟學家、有沒有經濟學都不影響社會。
但是,話說回來要經濟學干什么?我們之所以研究經濟學或其他的社會科學,就是我們相信理念在影響人的行為。再進一步講,過去經濟利益上的好多理解比較片面。我們認為利益是一種客觀的,尤其是物質主義的利益。這種理解是錯誤的。我們好多對利益的理解是通過觀念進行的,或者說利益是由觀念構造的。舉一個例子,好比幾十年前在中國被灌輸這樣一種理念,工人階級的利益跟資本家的利益是矛盾的,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和地主的利益是矛盾的。如果要追求利益的話首先要打倒資本家、地主階級,但是現在來看顯然這不是利益所在。當你打倒資本家的時候,全世界都是這樣,任何消滅資本家的地方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是最慘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是最沒有保障的。
再進一步看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完全是一種理念的產物,從馬克思最初對經濟的批判,到未來的社會應該是有計劃的協調機制,到最后斯大林,到中國搞計劃經濟。看起來我們都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這種理念錯了。計劃經濟制度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中國和蘇聯的災難是最慘重的,僅僅大躍進就幾千萬人餓死,這在和平時期真是不可想象。理念無論好或壞都會對人類發生重要影響,所以我們人類需要一種正確的理念去引導的。
我想講的第三點,就是思想的重要性。人類新的理念、進步的理念,只能是人類自身創造的。當然創造思想的人并不是平均分布,并不是像過去經濟學家講的那樣,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其實并不一樣,有一部分人比大部分人更善于思考,更能提出一些新的觀點來。這些新的觀點一開始是少數人提出的。這些人一定是很孤獨的,而且受到多數人的反對。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人提出的觀念不斷的被人們所接受。于是就變成了一種制度,我們就生活在其中。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思想和表達的自由對人類的進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扼殺了思想的自由、思考的自由,扼殺了思想的話,人類進步的種子就扼殺掉了。我們的所有進步都隱藏在新的思想當中。
我們知道,思想的自由競爭并不一定導致被普遍接受的思想一定就是最好的思想。因為要受到來自于人類本身無知的限制。我們接受一個觀點,最后也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是如果人類要避免犯巨大錯誤的話,不同的思想自由競爭是唯一的辦法。從歷史上來看,如果我們的思想市場是市場化的,非強制的,沒有一個思想可以長期的主導社會。如果施加了一種強制,使某一種思想變得壟斷之后,就會遏制其他的思想,會對人類的生活造成影響。像我剛才講的計劃經濟,再往前講,像中國歷史上思想市場最好的時期是什么時候呢?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那時候創造了燦爛的中國文化。但是到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是否定儒家的思想,再到漢武帝的獨尊儒術,這種思想都是錯誤的,無論是肯定它還是否定它。從此之后中國的思想就非常單一,除了到南北朝期間比較混亂的時候有新的佛教又起來了。無論是扼殺或者是樹立壟斷地位,其實都是對思想市場的破壞。
還有一個意思,人類社會的所有進步都是多元化的,包括觀念、思想的多元化是非常重要的。人類從生物學上是怎么進步的呢?一定是由變異引起的,變異就是跟之前不一樣。如果不允許變異,如果把變異扼殺掉的話,人類恐怕跟猴子差不多。新的思想就是一種對傳統的變異。我們知道在多元化的狀態下人類才能夠取得進步。
中國這二千多年停滯不前,為什么二千多年停滯不前?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思想被壟斷了。我們只接受一種思想,就不可能再進步。反觀歐洲是不一樣的,中世紀的時候是黑暗的,基督教的統治也是壟斷。但是在后期文藝復興之后不同的思想出現了,這才導致了他們的進步。這一點用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如果總是要追求一種思想,追求所有人有統一思想的話,中國不可能進步。所以思想市場非常重要。
我認為人類所有的自由里面最重要的自由就是思考的自由和言論自由。我們可以自己思考,但人類的思考如果僅僅是自己思考而不跟別人交流的話,你的思考不會達到一定深度的。只有在交流的情況下,你自己的思考才能到達一種深度。為什么說這個自由最重要呢?跟我前面講的第二個問題是相關的。沒有其他任何的強權或反自由的東西,只要允許人們思想的自由,可以避免人類很多的災難。比如剛才講到的五十年代的大躍進,只要可以實現思想自由,只要每個人可以在媒體上自由表達自己意見的話,大躍進是搞不起來了。即使有人想發動,有人追隨,有人就會反對。我們會看到好多事實證明這個東西是不對的,那么就會停下來。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國的好多災難都可以說是由于沒有思想市場、沒有思想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講,思想自由是人類所有自由當中最重要的東西。有了思想自由,專斷的、獨裁的權力其實都可以被摧毀。反過來也可以這樣講,如果要維持一種絕對集權的話,限制思想自由和消滅思想市場就是必然的。這是我講的第三個意思。
第四個意思,中國三十年的改革是功利主義主導的改革。兩百多年前英國經濟學家提出功利主義之后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功利主義講目標是第一的,為了目標可以不擇手段。只要目標是正當的,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在我們國家來講,這也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當然,經濟學家的目標是有一個社會福利或效率為導向。用在中國的話就是國家利益,只要我們認為國家利益是神圣的,所有對人類其他權益的侵犯都是正當的。好比說我們認為國家利益就是要經濟發展、快速的發展,快速發展的話就要去建好多新的高速公路、廠房設備,這時候就要有拆遷。要拆遷的話,因為我的目標是正當的,所以用什么手段拆遷都是次要的。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是功利主義政策。經濟學家論證要市場,因為市場提高效益,所以也是功利主義的。
現在到了這個階段,要從功利主義轉向一種權利優先或權利主義。簡單來講,人類有一些基本的權利,包括自由、人的尊嚴,無論出于任何目的都是不可剝奪的。西方經過啟蒙思想家的努力,已經形成了基本的共識。盡管經濟學家、經濟理論是很功利主義的,但是并不能夠動搖西方世界基本的權利哲學。由于中國沒有經過思想啟蒙的洗禮,所以這種功利主義一定是對人類基本權利的損害。
到今天應該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來。我們再看一些新的改革措施的時候,我認為不能僅僅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不能用GDP的增長來判斷某一個政策是好還是壞。當然我不是絕對的反對功利主義的,因為在某種情況下功利主義還是判斷標準、成本的計算。在人類的基本尊嚴、人權的問題上,我們不可以用功利主義。這種思想如果能夠成為很多人的共識,如果能夠成為政府制訂政策的共識的話,就可以避免由于發展而導致的很多負面的影響。現在社會的很多不安定因素都與個人權利的維護有關系。
我提出這個問題,也是希望大家去思考。我們未來真正的市場經濟一定是要基于個人自由、權利、尊嚴的基礎上。所有的政策不能越過這條底線。甚至未來對民主制度的評價,也不可以是純粹的功利主義。搞民主的話,我們比較一下印度。印度是民主國家,但是經濟發展很難,在印度修一條公路太難了,中國很好,效率很高,這種思路可能是錯誤的。當然也可以從功利主義的角度提出這個質疑來,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看,很多集權的東西看起來有效,做起來很強有力、很快見效,但是從整體不一定是有效的。舉例子來講,正因為這樣北京的城墻都拆掉了。現在到中國的很多城市去看都是千篇一律,我覺得這是功利主義的思維,也是跟政府有關系的。
我就講到這兒,謝謝!
Read/Edit >